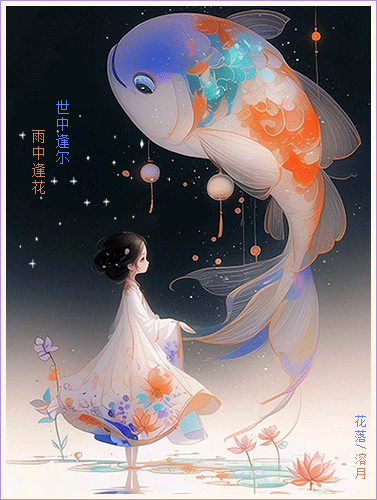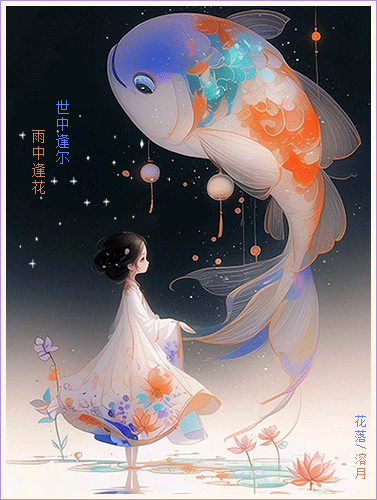|
|

楼主 |
发表于 2007-7-23 10:31
|
显示全部楼层
经纬
本来是想去喝茶看江水,结果懒懒的一车到了七星岗。在石板路上轻轻地走,手揣进兜里。
据说轻装以行,方能行之致远。据说我们必须很好地学会抛弃,才能很好地坚持行走。耳边清越的声音在叮嘱:不如远走高飞,自己解围。
我是无法飞起来的了,无心也无力突围,在十面埋伏四方楚歌里,剑光寒,英雄头颅离开身躯,作一生唯一的一次翱翔。在行走中,一瞬间,我感觉自己庄重得象一个慈祥的父亲,拼命地掩饰曾经失去的悲伤,为了现在的成长,就注定选择遗忘。
进了若瑟堂,零散的有几个人在做礼拜。一个老者默默垂首,一对男女并肩肃立,还有一个我,在门边。
乳黄厅灯,无语烛花,隐约圣歌。混合成安详的水银冉冉泻地,一步一个天堂,一步一个上帝。选个位子,重叠双手,清晰地感觉到自己身躯折落的沉重,与神对视,心里悄悄:“我不信你,但是我想亲近你,我知道,我们都是你的道具。”
恍惚中,慢慢起来,慢慢出来,慢慢离开,回头再望一眼哥特式尖顶孤独地直刺灰蒙蒙的天空,它想必知道它的名字隐藏着一个故事,一段逝去。而必定有人,在天空或者,我的心里。
问余何意栖碧山,笑而不答心自闲。
知音本来少,知音本来短。孤舟渡大江,东流的仍自东流,靠岸的自去靠岸,两者在相交那一瞬镌刻依恋;飞鸟栖青枝,飞翔的还要飞翔,扎根的依旧扎根,两者在相依那一刹验证永恒。最完美的情绪,无非是最残忍的宿命。
弘一法师在西风长亭下笑问,“随处做主,随缘即宗;竿木傍身,逢场作戏。有么?有么?”我不知道。只想把某些名字写于纸笺,在每一个冷的晚上,夜放乌鸡带雪飞,朝伊飞奔。
以光阴为经,以眷恋为纬,编个篮子来藏情,一路走去,一路收拾。 |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