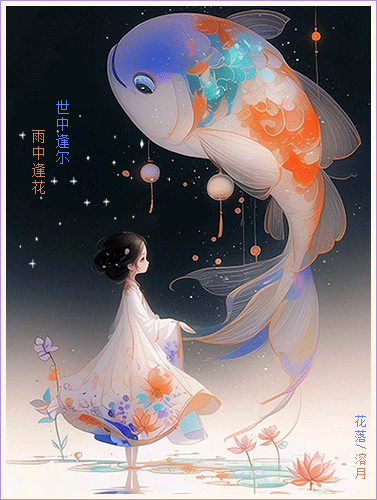|
|

楼主 |
发表于 2015-12-23 09:19
|
显示全部楼层
今冬多阴雨,窗外始终云迷雾锁,灰蒙蒙的,像一个阴郁至极的人,怎么哄也打不开笑脸。
林徽因:“话从哪里说起?等到你要说话,什么话都是那样渺茫地找不到源头。”写字也一样。昨天下雨,自外地坐车归,隔着水雾锁住的车窗和一层层雨帘,看似有似无的田野,楼宇,一陇陇,一幢幢从身侧滑过,慢慢睡着了。醒来对着布满水雾的玻璃窗,忆起曾经玩过的河沙滩,一样的可写可画,起了童心,动了几下手指,在玻璃上抹了几笔山峰,到底不会画画,虽也层峦叠嶂,实在丑极,索性擦了,车窗一下子变得清澈透明起来,真实的青山刹那间一座座的从窗外一滚脑涌了进来。进山了,近乡情更怯,当时想下车后写点什么,今天对着同样阴沉的窗外,昨日之幽思渺无踪迹,人虽坐定,无从下笔。
车窗也好,屋窗也罢,隔着窗子看景,大抵还是隔了一层。这隔虽不是“酒在肚子里,事在心里,无论喝多少酒,都淹不到心里去。”,总也相当于隔着手套抚摸美人脸的隔。还是走出去的好。可又能走到哪里呢?窗外大抵还是窗,“不管你走到哪里,你永远免不了坐在窗子以内的。”不过恰是因为一隔,多了层朦胧,倒也适合阐发幽思。
玻璃窗是后来的事,我少时的窗是木窗,以木为格,糊纸为面,从内对外看,只能看到一些阴影的轮廓。悬梁上的蛛丝摇摇欲坠,窗下的少年掩卷发呆。风景在窗外,热闹也在窗外。如同当日隔着发黄的窗纸看窗外,今日怀想童年,朦朦胧胧的,忆不真切了。渐渐的大了,渐渐的为生活而到处奔走,从一扇扇窗下,移到另一扇扇窗下。窗的本质是自私的。想看景了,打开;想通风了,打开;不想看了,或是不想被看了,就关上。一扇扇窗子里发生的事,拢起来,便是人间。
偶尔有愚笨的念想,跳出人间,做和尚去。看汪曾祺《受戒》,方知当和尚也不容易:“一要面如朗月,二要声如钟磬,三要聪明记性好。”对照三样,我没一样合格,亦也没有一个明子那样在庙里当方丈的姨父,不由断了这念头。何况,庙也是开窗的,到底逃不脱人间。芦苇荡那节,当英子追问明子时,我心下着急,恨不得帮明子答了。及至后来看到他俩划进了芦苇荡,我也开心起来。
爱占上风的时候,会忘记一切,会痴念人间最美不外于一扇窗,两个人。无论窗内窗外,东窗日升,西窗日落,还是天窗上的星星,夏日吹风,冬日烤火——共食那寒冬最美味的水果,想想,干什么都适宜。莫奈何到隔窗互望,也自有一份凄然的欢喜。你从窗内看山,我从山上看窗,也有着一股股暖意,也能从旭日傻傻地看到昏黄。
纪伯伦:“我的兄弟呀,你的精神生活被孤独和寥寂所包围,假如没有这孤独,你就不会是你,我也不会是我;假如没有这寥寂,我即使听到你的声音,也会以为是我在说话;即使看到你的面孔,也会以为是我在揽镜自照。”其实,风也萧萧的窗外,亦无佳人,亦无流响,冬来欲雪。 |
|